余光中翻译的“王尔德四部喜剧”是《不可儿戏》、《温夫人的扇子》、《理想的丈夫》以及《不要紧的女人》。
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,1928年生于南京,21岁时离开大陆到台湾,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。其人“左手为诗,右手为文”,出版诗文及译著近四十种。通晓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等多国语言,翻译作品极为丰富。著有诗集《舟子的悲歌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散文集《左手的掌纹》等。他被台湾文艺界尊称为“诗翁”。
8月25日晚,满头白发的著名台湾诗人余光中现身大型诗乐晚会《深圳梦典》的舞台,用诗歌将这个属于鹏城而立之年的夜晚变得意义深长不同凡响。这是余光中先生第二次来深圳,他第一次来深圳是在三年前,他应邀在读书月期间登坛演讲。当时,深圳特区报记者曾与余光中先生就散文创作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话,而此次来深是为诗歌而来,于是,我们的访谈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诗歌。
余光中回忆说,“我一生经营四大文类: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,我把这称作自己的四度空间。而最早出道的,是诗歌。我的第一首诗《沙浮投海》写于南京,当时只有20岁。”老人家声音不高,思路敏捷,语言清晰,娓娓道来,于是,一位老诗人与诗相伴60多年的诗意人生,就此旖旎铺展开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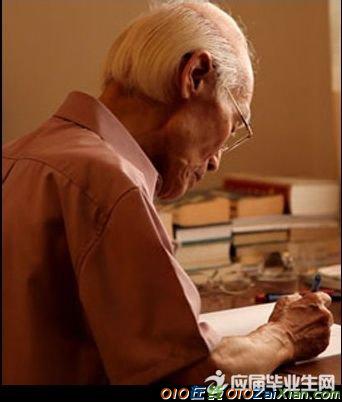
诗歌有国界
记者:余先生,您是学外语出身,精通西方诗歌,同时对中国古典诗歌造诣极深,那么,您在诗歌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呢?
余光中:西方语言中代名词、介词很多,中文比较少。而且西方文字常常使用表示身份的字眼。中文说“我吃素”,只是一个短句;而比较西化的人会说“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”。像生物学家、宇航员这样表达身份的字眼,西方特别多。所以西方语言名词多,中文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用名词。“我吃素”,侧重于动作的表达。我自己写诗,也翻译了很多英美的诗,自己觉得就好像跟西方的武士打斗,只有学会他们的一招一式,才能让西方的好东西反过来进入我的诗,成为我写诗艺术的一部分。所以,我认为翻译对诗歌创作很有帮助。
记者: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语言载体中哪一种在诗歌当中更有力量?
余光中:只能说中文的优点往往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,西方语言的若干优点也是中文所没有的。举一个例子,比如说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: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,直译给很多美国学生听。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,问我,为什么你们中文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?“松下问童子”是谁在问?“言师采药去”又是谁在答?“只在此山中”的人是谁?“云深不知处”是谁不知处?他们显得很迷惑,我说对不起,就把所有主词都填进去了,问他们还喜不喜欢:“我来松下问童子,童子言师采药去。师行只在此山中,云深童子不知处。”我想我们中国读者一定觉得还是五言比较好,改成七言就过于繁琐累赘,人称交代得太清楚,反倒没有韵味了。
中文的美感来源于朦胧和散漫,否则李白那句诗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销愁愁更愁”就不会这么经典。他把水重复一遍重复得有韵味,没有用代名词。如果变成“抽刀断水它更流,举杯销愁它更愁”,这个味道就是英文的,不是中文。每种语言有独特的表达方式,写中文诗歌要发挥中文的优点,写外文诗歌要发挥外文的优点。
记者:您先后几次赴美,创作上显然受到西方诗歌创作的影响。您曾说自己“笔尖所染,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,便是泰晤士的河水”。但您诗里也有“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,怎撼动你悲壮的楚辞”。这是您有意识的一种反证吗?您曾说过,相对于西方文化,中华文化更具有弹性。可否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?
余光中: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讲过这句话,这当然是很主观的意见,应当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讲的。西方文化也非常多彩多姿。不过,如果要讲弹性的话,我们中华文化最大的弹性,就是以儒家为主,以道家为辅,后来还加上佛家作为调剂。入世很深的人大都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,而在野或者失意的人,倡导出世的道家可以给他们以慰藉。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,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,可是文学艺术绝对不能限制在基督教里,它有时会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统中去。一个国家的文化有主流有支流,文学艺术往往从支流中吸收更多养分。这就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弹性,能够允许多种支流共生。对于中华文化来说,就连外国文化也能够变成我们的一条支流。
记者: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融会贯通成就了您的诗歌艺术?
余光中:我还不敢说融会贯通,只是接触得比较多,写诗的时候就能够作为一张王牌,至少是多了一个筹码。
本文来源:https://www.010zaixian.com/wenxue/yuguangzhong/218148.htm